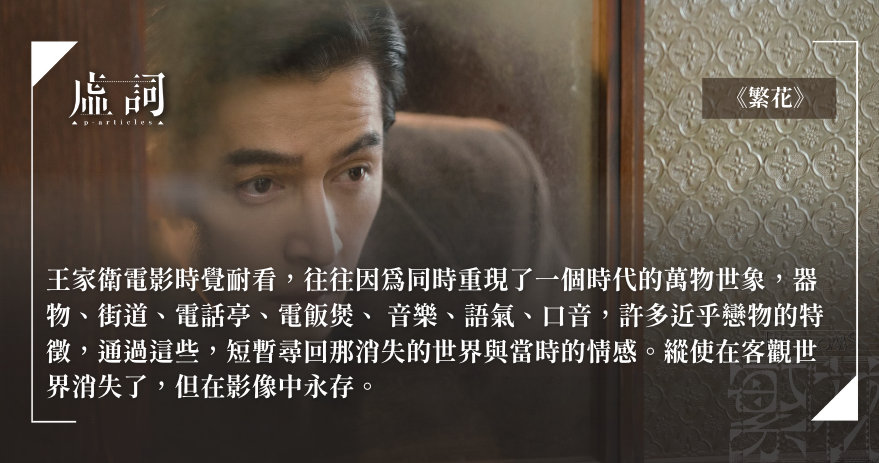繁花番外:王家衛的執念(上篇)
影評 | by 李照興 | 2024-02-08
0
《繁花》開頭,要上閣樓。還要在夜裡,不易。但過了兩層,就會好。就如追劇。
有人未看完開頭兩集就棄追,受不了那密集對話與調高聲綫的上海話(當然要看上海話版)甚至劇情表面的流水作業情有可原。不過說它不依原著就肯定不能當為理由(第一次睇王家衛咩!)。
戲過三巡露兩手藝高真章兼「一代宗師」式傳承(今次講商業經不是武術),加上越發爆款的劇中元素全城考古更是始料不及。只能說王家衛在建立他的敘事宇宙及各種認真考究上還是出手不凡。不過由電影到電視劇的格式轉換中卻不得不作出取捨,甚至是力圖取悅卻又被認為是不夠接地氣的中國電視劇元素。但以年代劇來評判,它最大的問題反而是外形上處處展現的懷舊或還原,基於眾所皆知的內容制約(可以說改革開放政策的成功但難以說有此政策改變之原因)只能流於表面,亦即真正令那時代生機煥發的時代原因難以述說,那當然也是中國大陸內全面討論這劇時的盲點。但那時代曾經的一分為二,嘗試國退民進而非反過來,商業與個體釋放的動力,才真是那時代繁花盡放的原由。對比今日當又是另一循環。
1
那是1963年,和十多年前斷續離開那座城市的家庭一樣,有些覺得不會等太久就能回去,又或者留下的家人很快會出來團聚。然而時代就此關上門,留在上海的不單是王家衛的哥哥姐姐,而是他所不清楚的故事另一端,有關自己的家庭,有關於上海。
如果真有王家衛上海香港電影宇宙的話,《阿飛正傳》、《花樣年華》和《2046》是構成他那代上海人在香港的故事,但就像一幅封塵後重現的家族與城市拼圖,來去端詳,總有那麼幾塊缺失了,六十年代他離開之後的上海到底怎樣了?
所以大可以想像,多年後當王家衛讀到金宇澄《繁花》開頭之時:「獨上閣樓,最好是夜裡。《阿飛正傳》結尾,梁朝偉騎馬覓馬,英雄暗老,電燈下面數鈔票,數清一沓,放進⻄裝內袋,再數一沓,拿出一副撲克牌,捻開細看,再摸出一副。接下來梳頭,三七分頭,對鏡子梳齊,全身筆挺,骨子裡疏慢,最後,關燈。否極泰來,這半分鐘,是上海味道。」他大抵知道若真要講那未完的故事,就得回上海講。也是好多年後,我才得知,這個「上閣樓」,要在夜裡的說法,是舊日做地下工作者的密碼。
這些老上海派頭,早也構成了王家衛作品的特色。時刻雍容的潘迪華一時南來貴婦一時包租婆,說一腔連今天上海年⻘男女都認為是老派的上海話。語言與街道的消逝,兩者合起來,就是時代情懷,也就是這種情懷被完美的嫁接到王家衛的作品世界中。
那一點共通,王家衛曾經告訴我,是一種「人面桃花」之嘆。當我們看《阿飛正傳》、《東邪⻄毒》、《花樣年華》、《2046》、《春光乍洩》到《一代宗師》,有一種情感意象常能引起共鳴,正就是那種時不我予,那種機會錯失,一種遺憾,但又似乎是時代變化的必然。人在其中,回過頭去看,縱使地景似然,但早已物是人非,只有桃花依舊笑春風,這「人面桃花」正是王家衛要表達的意象所在。
是那個終於响得珊珊來遲的公眾電話亭中的電話,那個回不去的白駝山,那吳哥窟的遺址,那孤零的酒店門牌,那本來計劃是兩人同往但到最後只得一人抵達的瀑布。
2
這種人面桃花之慨,對於當年由上海到香港的圈子而言尤為熟悉,這也是王家衛長期關照的命題, 其實是關於流徙,由是鏡頭之下,盡皆過客,乘搭不同交通工具,永遠在移動之中。無論是地理上 的從北往南(不僅是由上海至香港,《一代宗師》述說的更是中華武藝的南北融滙傳承,最終葉問再傳李小龍而後走遍世界。或問,一個五歲就離開母城的孩童,真的會對已離開那麼久的城市這麼上心嗎?母語之外,可能還有幾代上海人流徙基因的使然。不要忘記,從三十年代開始,基於不同原因,由達官貴人、廠家商販、文人戲子到黑道頭目,多數都為避禍,上海人及其 資本就斷續南移香港。在那時代,這批南來客愛聚居於尖沙咀和北角,也是活在一個隨身攜帶的香港小上海。
這些上海人在香港的故事,在王家衛電影世界中的六十年代中曳然而止,對於更多的劉以鬯及王家衛們,那一個上海來客初來埗到的時代已經遠去,走散的上海人及其傳奇,在現實裡卻是一分為二,正是又回到王家衛的家族史一樣,一支在香港,另一支留在上海(其實該還有第三支,是去了 台灣,那故事早已由白先勇寫下; 以至到今日可能有第四分支,即流散全球,存於其他海外華人世界)。
在此上海人(或更大程度上指華人)的離散背景下,看《繁花》才更突顯意義。更多沒有離開的人,在上海本土延續王家衛的上海故事,剛好也就是《繁花》的情節,這代人於七、八、九十年代 伴隨上海的新生,外灘開始了倒賣泊來貨,黃河路酒家林立,不遠處就是上証交易所。彼時上海人交叉的路軌,再一次和香港息息相關。不少上海家庭,都會有親友在香港。離開的人,後來又有機 會陸續「回去」,探親的,送日用品的,後來做生意的,嫁娶的。上海香港,雙城對倒命運不變。
3
看熱鬧都聚焦劇中的黃河路。說王家衛鏡頭下的九十年代初上海黃河路,霓虹招牌太多太亮了,現實中當時哪有那麼光鮮。當然有關在政府單位中的工作情況也較脫離現實。另外還有故事沒依原著《繁花》的人物眾多散點憶述,而是只集中在胡歌飾的阿寶這一位男主角發跡史,伴以三位女主角情感和各自背景故事,以及一個上海「老法師」做生意前輩作略帶神秘的重點貫串。意思是說他改得不夠原汁原味,但這點對看慣王家衛作品的人而言當不用解釋。
對於黃河路的論點,王家衛的答覆頗有意思,就是他要重塑的,並非當年真實的黃河路,而是當年上海人初見黃河路那盛景時的不真實和震撼感覺。言下之意,不真實才對,要造就的正是那種假假地的虛幻氛圍。
問過一些當年真經歷過的人,視覺景象和色彩,當然是電視劇顯示得過於光亮濃烈,不過大抵記得那種新興的新時代繁華,是沉寂了幾十年的上海從未有過的。不僅新店林立,沿街熱鬧,各種豪華菜式或新引入的港式風氣滿布整條街上百間食肆。賺到第一桶金的人在這裡慶祝,或者傾談更多的大生意,其實都蠻像《金手指》中那七、八十年代的香港。
我要到2000年之後才到黃河路(距人民廣場不遠),那時仍是主要美食街,不過就沒有劇中那些大富貴豪華飯館了,反而在港人遊客圈中知悉,最吸引的目的地,是街上的佳家湯包,一家手工現造多汁小籠包的小鋪。豪華的館子則擴散到外灘,偏向西式,面向的是更國際化的消費群。
現實中,九十年代初港商在上海的飲食和生活足跡其實尚未很大幅擴散。但所謂早期港式則體現在那些傾生意的排場和浮誇的菜單上。因為大家開始下海做生意,民間生意中較大的都和外貿有關,那接待港商就成為重要一環。而港商也把八十年代港式粵菜奢華風帶到上海。 《繁花》有段情節頗誇張但應有根據,就是港商組團考察,香港大家族都得自帶廚師,因為老細們口味嚴格,去哪都得有專人照顧,當然順便也是擺擺款以示威勢。這點上海生意人最受。
劇中一幕是中心場景致真園被黃河路一眾老板杯葛沒有廚師也沒人肯供應食材,有辦法的高人就靈機一觸找來正值到上海考察洽商的香港大亨借用其廚師團去改做高級粵菜迎客。幾道港師傅名菜仙鶴神針和大王蛇一戰成名,從此港式浮誇粵菜在上海大行其道。
據幫此劇做文學及背景資料搜集的好友提醒,她作為80後,那時代在上海確是有種對豪華菜的幻想,年青人聽得去黃河路食頓豪華美宴都算得上完美生活。夢想是請客叫龍蝦三吃,另有椒鹽大王蛇,算是其時的下館子請客最高指標。可見耳濡目染傳聞正盛真的塑造大家的期望。
講來她在《繁花》劇組做足七年功課,專搜資料去嘗試設定劇中需要用食物餐宴的話該如何準備。那包括了當年有什麼菜單,用什麼餐具,排場如何等等。就算最終不放到拍攝內都真是當作歷史考掘收獲豐富。
最富現場感,是說要備泡飯,導演當然要熱騰騰冒烟的鏡頭,但備料廚房在遠處,劇組只能把飯做得熱辣,用厚碗附蓋盛載過來,等到拍攝時,胡歌一口吃下去,差不多都把他燙到。
4
還原一個時代,首先,是確保物的留戀。 小說雖是六十年代講到九十年代,可今次先集中在九十年代阿寶變成寶總的一段,還有身邊的女子。不得不這樣集中,原著上百個人物,三大男主,除了阿寶,還有小毛和滬生,各自又搭上出出入入諸色人等,用小⺠城中生活去看城市幾十年變化。挑戰是部份上海方言用語(其實不是如誤傳的全書用上海話寫成),如何確切轉化到影視作品中。若要傳神,那可能是部全上海語的作品。於是找資料找景之外,找會講上海話的演員成為一個硬需求,於是有了男主胡歌、女主馬伊琍、 唐嫣的選擇(中國現一綫最聞名能操上海話的演員其實是徐崢)。
資料搜集老早就像歲月偵探般打聽那個時代上海人生活的每個場景。人們吃些什麼,看些什麼,住在哪。金老的小說最看得眉飛色舞是寫轉彎抹角走走逛逛上海街道弄堂小館公園公交站鉅細無遺, 由茂名路思南路國泰電影院到長樂中學,像一大本上海上只角地理誌。如果有一天,上海這個城市 消失了,人們可以憑《繁花》的文字把它重建。
5
後來只能搭景再現舊時上海,不過怎都要參考一下,上海富當年生活色彩的老弄堂到底還有沒有?去菜場、里弄、市集什麼的,現在哪能弄出一整個真的舊弄堂來拍假的當年戲?
記憶與書寫所以重要,因它才有可能重組一個時代。原著中有張上海盧灣區手繪地圖,而現在已再沒了盧灣區了,被拼到黃浦區,正如後來閘北拼進靜安。情況可能等如有一天,說銅鑼灣區沒有了,都 拼進灣仔區,名字不一,那我們的銅鑼灣還是銅鑼灣嗎?(當然我們知,從行政區而言,確是沒銅 鑼灣區這劃分,不過我們不能否認有這個⺠間劃分。)
6
離開的人,後來又有機會陸續「回去」,探親的,送日用品的,後來做生意的,嫁娶的。 看過《繁花》的,一定會記住那形容: 不响(書中出現過千次)。這才驚覺,這種上海式的不响(不是單純指 「不作聲」而是表現多種態度的可能性: 不悅、不從、不表態、無聲抗議、逃避、裝糊塗等等),也是早早在梁朝偉的沉默與猶豫中領教過。 人之外,還有空間。小說《繁花》開始於《阿飛正傳》最後梁朝偉小閣樓梳頭袋錢整裝待發一幕。 又或者那些《花樣年華》走道穿梭,實則也像上海庶⺠的尋常生活空間比例。狹小,曲折,聽到隔屋的聲响。
7
都是時代中微小個體的絮絮不休,行來行去,蜚短流長,直到時間與城市化為灰燼。於是,《繁花》可能變成那個更大的故事,由《阿飛正傳》、《花樣年華》、《一代宗師》拼砌的那個漂流到香港後漸漸融進為香港一代的那故事,於某個歷史時刻的一個分叉口,像花園小徑生出的歧路,導回到沒有漂到香港的那個平行世界。香港故事早早滲進別的城市的故事,同時,香港同樣成為了他方的故事。 不同的是人們的選擇,地域的區間,相同的是,那種事隔多年後回看,人面桃花的熟悉又陌生感。 王家衛電影時覺耐看,往往因為同時重現了一個時代的萬物世象,器物、街道、電話亭、電飯煲、 音樂、語氣、口音,許多近乎戀物的特徵,通過這些,短暫尋回那消失的世界與當時的情感。縱使在客觀世界消失了,但在影像中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