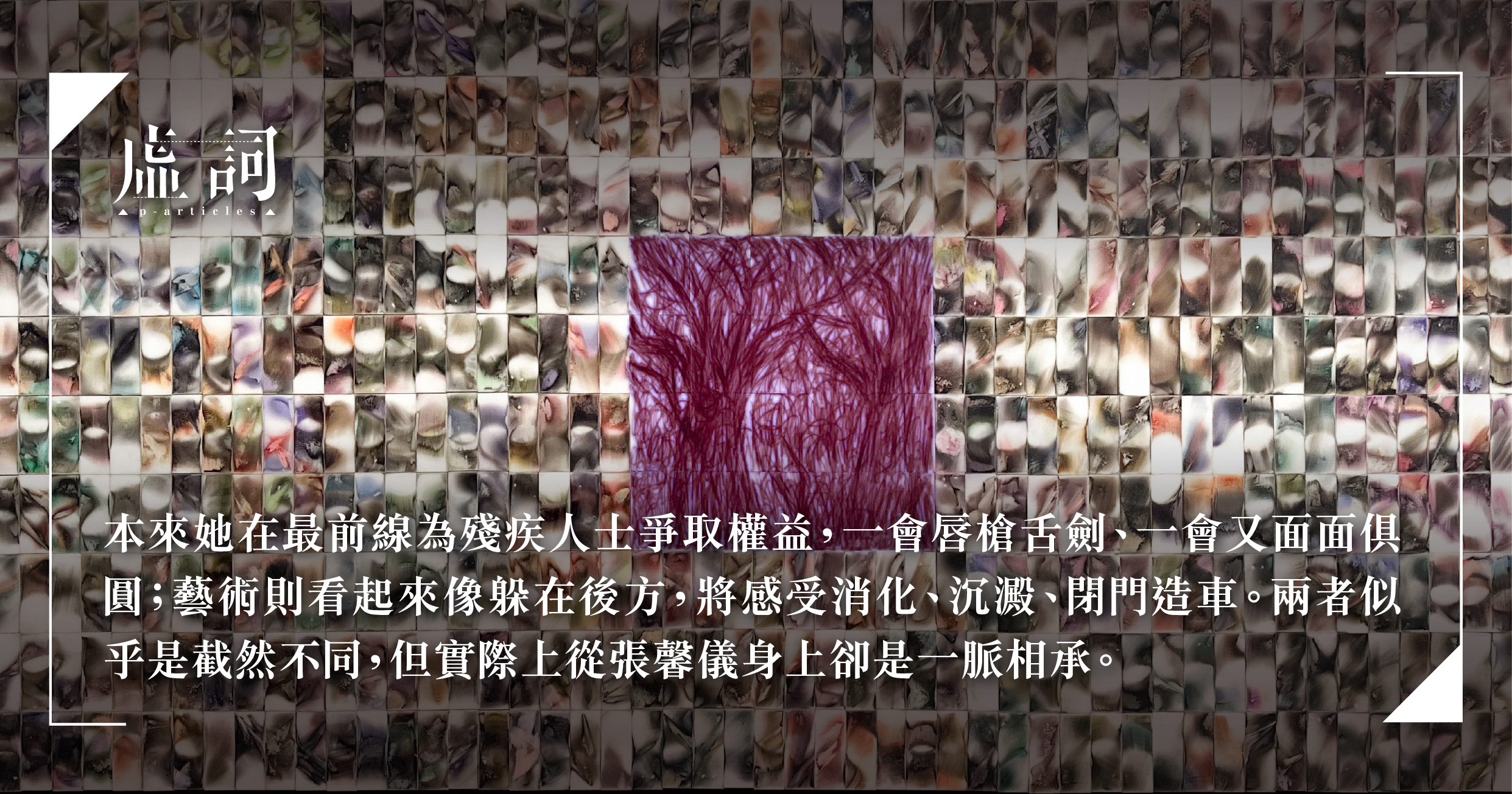唯一的人就是所有的人——談張馨儀的藝術
藝評 | by 馮以力 | 2023-09-18
「不能說它是紅的,它不是一種顏色,它只是蘋果。不能說它是圓的,它不是一種形狀,它只是蘋果⋯⋯」藝術家兼詩人張馨儀推薦谷川俊太郎的一本散文集《定義》,當中有篇《對蘋果的執著》,通篇都是試圖用語言來形容蘋果的所有但是註定失敗。無論從哪角度嘗試切入,始終也不能完全用語言來把握蘋果的一切,但人類又很喜歡用語言來理解和詮釋事物,甚至以為語言就是框定了那樣事物的全部本質。
定義蘋果如此,定義人也如此。
從過往一些訪問、畫廊的介紹中,不難知道張馨儀曾是一名精神障礙者,在她以藝術為主業之前更曾一直致力進行精神障礙者權益倡議工作,並創辦了非政府組織「殘疾資歷生活館」——如果大家沒有聽過「精神障礙者」這個名詞,那以香港人一般的說法,多數會指「精神病人」;亦由於大家稱之為「病」,理所當然經過「治療」之後便有「精神病康復者」。
我不會說「精神障礙者」與「精神病患者」兩者是指涉同一些人,「係個名唔同啫!」。不,不是的,否則張馨儀不會以過來人身份編著《殘疾資歷:香港精神障礙者文集》,香港本地第一本由精障者主導,嘗試不以純醫學和健全主義角度探討「精神病」的書。殘疾的「資歷」即是運用自身殘疾經驗至成熟,轉化為社會各層面革新的資源,豐富了「殘疾」之意義。
不過,面對著一個龐大的文化認知規範,倡議、出版、宣導等等正路的權益爭取行為不是完全無用,但張氏坦言空間仍然不大,於是在這領域工作了十年後毅然全心轉向投身藝術領域,於2020年完成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藝術學士,亦在2022年於倫敦大學金匠學院榮獲了應用人類學和社區藝術文學碩士學位。
本來她在最前線為殘疾人士爭取權益,一會唇槍舌劍、一會又面面俱圓;藝術則看起來像躲在後方,將感受消化、沉澱、閉門造車。兩者似乎是截然不同,但實際上從張馨儀身上卻是一脈相承。除了她自小已酷愛繪畫之外,她之前倡議精神障礙者重奪對自己生活之主宰權(也就是嘗試撼動社會對「精神病」的定義),與當代藝術中對一切框架的質疑這套常見進路,其實兩者的思考是不謀而合。張氏為人熟知的作品是用擦膠從不斷擦掉報紙的過程中,擦膠身上吸取油墨,竟渲化成斑爛的顏色,拼成一幅新的畫。原本擦膠一般用來「減」的功能突然轉化成「加」,變成了畫筆同時又是畫布,報紙則是調色盤。「擦掉 vs 著色」、「消除 vs 保存」,一如「殘疾」似乎本是「反」,「資歷」則是「正」,兩矛盾者之「合」提醒了大家原來可以不用二元思維來看這件事,回歸自我之主體後便是化解、超越、昇華。
擦拭報紙與身分之無差別心
張氏對擦膠這種物料的探索大概始於她的兒時記憶:父親為每個乒乓球學生度身訂造球拍,他總會把正方形的、或紅或黑的保護膠膜剪裁然後貼在球拍,所以家裏儲起大量膠膜。畢業後她在學校教兒童美術時也開始收集學生使用過的擦膠作為記憶和活動痕跡。而在2019年間,由於手機投擲出來的時事訊息量太巨大和難受,令她幾乎窒息,她反而跑到圖書館裡看報紙來閱讀新聞,因而想到了將擦膠和報紙結合的創作方法。
當然,將報紙的新聞「擦掉」這種行為,本身已極富符號象徵意義,我們也確實可以以文化角度閲讀她的作品。報紙作為傳統的大眾傳播媒介,最直接的功用是記錄前一天發生的重要事件,因此「擦拭新聞」即時浮起的疑問便是傳媒的話語權問題——誰主真相?——是誰有權編寫新聞?誰界定甚麼事件重要值得記錄?誰決定一件事件的切入角度?新聞的影像又在訴說著甚麼?當我們面對著只有事件名稱但沒有新聞內容如〈擦拭新聞:珍寶〉(2022)這幅作品,我們意識裡對珍寶海鮮舫這件事又產生了甚麼回憶和想像?這些回憶和想像又是如何建構的?
〈擦拭新聞:珍寶〉, 2022
報紙墨水和橡皮擦
58.5 x 35 x 1.5 cm
再問下去,自然會發現報紙更深一層的意義也可以在於——像社會學家、《想像的共同體》一書作者班納迪克.安德森指出——用來維繫「族群的想像」,從而使族群有能力隨著宗教式微取而代之成為人生意義的歸宿:族群填補了意義的空虛,偶然(你不能選擇出生地)成為必然(你出生在那裡必然是那國的人),繼而你便有該族群給予你的身分所帶來的義務。我們本來無可能認識所有同族的人,何以能為陌生人出生入死?安德森認為報紙的威力在於向該地域的人將本在線性時間線發生的不同事情呈現於同一個時間點之上,這樣那些人便因閲讀同一事件而建立了聯繫,正如我讀到了珍寶海鮮舫沉沒的新聞,會想像這裡的人也能讀到同一件事並分享類似感受,從而與本毫不相識的人建立族群身分認同。張馨儀分別用了600和800多塊擦膠拼合的作品〈擦拭新聞:電光火石〉(2022)和〈擦拭新聞:風吹草動〉(2021-2022),當時她住在倫敦東南部的Eltham時為撰寫論文而進行有關去殖民化的心理健康調查,擦拭的對象是2021年12月至2022年3月期間出版的英國報紙。既然報紙本有建立族群想像之用,將它的內容削減到只剩下抽象的色變,看起來與任何地方的報紙擦拭出來不太相異,那作品中的擦膠那種介乎加減之間的中間性(in-betweenness)散發出來的曖昧,令人聯想到香港夾在中國作為「祖國」和英國作為前宗主國之間的身分浮游,似乎隱含著人先存在才有身分(以及隨之而來的定義、規範、框架)之存在主義意味,所謂必然其實也只是偶然。
〈擦拭新聞:電光火石〉(2022)
報紙墨水和橡皮擦
68 x 64.5 x 1.5 cm
〈擦拭新聞:風吹草動〉(2021-2022)
報紙墨水和橡皮擦
114 x 51.5 x 1.5 cm
正如安德森指出報紙為人類建立了一個與古代上帝視覺式截然不同的時間觀,記載著一件又一件的「事件」,碎片化地散落在我們的人生認知中。當代哲學家齊澤克在《事件》一書中寫到:
負面概念容器將構成歷史偶然性向形式結構轉化的標記點——在這個節點上,形式結構落入了自身的內容之中,從而成為偶然性的事實。形式結構自身沒有時間維度,而偶然事實的層面則是事件性的,換言之,後者屬於那個變動不居、朝生暮死的偶然事件之域。
報紙的壽命通常只限於一日,成為舊報紙後作用非常有限,是名副其實的朝生暮死;藝術固然就是形式結構,而張氏的擦拭作品就是那個容器,將一段段的歷史偶然一下子鎖進了沒有時間維度的永恆之中。張氏喜歡引用海德格視時間不是外在於人類的一個客觀框架,而是人類根本是由時間構成。因此,沒有時間維度的狀態是非人的,〈擦拭新聞:夜中霓虹〉(2022)表面上緣自疫情下城市再不需要霓虹夜燈,只遺留在報紙的記載裡。擦拭後呈現的不再是人類的回憶,而是超越了人類架構,作為一種前人類、前宇宙的稀薄狀態。
〈擦拭新聞:夜中霓虹〉(2022)
報紙墨水和橡皮擦
68 x 64.5 x 1.5 cm
消融——「甚麼也不是之人」的尊嚴
誠然,創作方法加加減減在當代藝術的實踐中並不少見,對文字和圖像的「減法」形形色色,用擦膠擦去新聞老實上說是千萬種的減法之一:塗改、裁剪、模糊化、燒燬、沖洗⋯⋯甚至誤讀、偽造等,五花百門,各種方法各有意思。但如果只是為了求新,又何嘗不是跌落藝術創作或藝術品是為了服務於藝術史的大論述?還是提醒自己回歸到每個藝術家作為活生生的人的背後故事。尤其張氏似乎並不單從「混合媒介+文化意義」的創作方程式來對待報紙和擦膠,從她作品中並不展示被擦的報紙的抉擇便知一二;她偏向以繪畫的方法來運用這些物料,她坦言在2023年新個展〈時拭迴〉的作品多內化了她個人歷史的經驗,不同於以上2022年那批結合社會事件影響的作品。而她對於擦膠擦拭報紙的技巧也不斷磨鍊到如傳統繪畫般一樣細膩且多變,例如新作〈擦拭新聞:從氣根釋放氣體〉(2023)她的擦法趨向雕刻的刀法,每次只往同一方向傾斜地擦向紙面,形成較剛勁俐落的線條,彷彿與作品的主題榕樹交錯的氣根相呼應,勾起她從前身體痙攣時找到公園的長椅和樹蔭作為她及時的避難所之感覺。
〈擦拭新聞:從氣根釋放氣體〉(2023)
報紙墨水和橡皮擦
87.5 x 57.3 x 1.5 cm
又如一個個聲納般的構圖,〈擦拭新聞:躺臥在皮革梳化上的氣流聲〉(2023)是張氏憶起耳朵貼在皮質沙發表面上,聆聽著她移動時從靠墊傳來的嘶嘶聲所帶來的孤獨、放鬆和投入於聲音和觸覺的溫柔感覺之記憶。每件擦膠的色彩比起2022年的作品偏暗黑但更沉實,看似描繪那寧靜時刻釋放出的風聲旋渦。更密閉、幽邃的是〈擦拭新聞:護土牆〉(2023)和〈擦拭新聞:在夜晚的公園中哭泣〉(2023),兩者像滲透著一種像雨後濕漉漉的植物和泥土味道,張馨儀在中學時被診斷有精神分裂症,情感在家裡只能隱藏,需要離家到公園尋求心靈的平靜;而現在創作則是將當時宣洩內心情感的回憶視覺化,在報紙上擦、擦、擦,擦膠上色之外同時消解她累積多年的矛盾和痛苦,尤其作品〈在夜晚的公園中哭泣〉中的虛白源自當時公園中的燈光,看起來彷彿四周凝視著自己疑幻似真的眼睛,不知是否暗示著歷來社會上投在她身分上的目光。
我讀到《殘疾資歷》時很深刻的部分是它引述一名德國精神科醫生寫的:「這個世界上,其實沒有精神分裂症,沒有抑鬱症,沒有成癮症,有的只是承受著不同痛苦現象的人。」我想這個城市裡每個人或多或少也有些傷痛,也因而需要一些排解。當不再以醫學分類,大家在痛苦面前其實是平等,所以張馨儀在〈時拭迴〉展覽中的另一房間展示她很個人的那張由精神科醫生開出的康復證明書正正並不是想觀眾用醫療框架去看待她和其創作,而相反是希望直視過去而超越過去,從一個整全的時間同時性(simultaneity)將過去和未來都聚於她的當下。說到這裡,應該會更感受到她由一個人權倡導者轉向做藝術家的因由,藝術那種從意識上長年累月的改變,雖然沒有搞campaign、project那些objectives和數據去check the boxes,藝術無形亦不自知,但先處理好自己心情,才去處理事情,釋放出來的人格力量可能更大。
〈擦拭新聞:躺臥在皮革梳化上的氣流聲〉(2023)
報紙墨水和橡皮擦
58.5 x 51.7 x 1.5 cm
〈擦拭新聞:護土牆〉(2023)
報紙墨水和橡皮擦
58.5 x 51.7 x 1.5 cm
〈擦拭新聞:在夜晚的公園中哭泣〉(2023)
報紙墨水, 原子筆墨水和橡皮擦
43.2 x 100 x 1.5 cm
張馨儀坦言對鑽研擦膠這種物料的著迷程度已成為她的根。除了常用的擦拭外,較早期時她也試過童趣地用鉛筆在擦膠上戳洞(想必很多人兒時也曾在上課時無聊這樣試過),拼合起來遠看竟像一幅現代水墨的〈點現〉(2019-2023),像皮膚充滿千瘡百孔般的敏感和脆弱,原來是呼應著她年輕洗澡時感覺自己像被監視的時刻。近期則有些擦膠作品她索性完全回歸純粹的繪畫思維,用原子筆在擦膠面上直接繪畫,〈枯榮II〉(2022)和〈擦拭新聞:豬籠草〉(2023)更是具象畫,後者她將豬籠草——她曾被順勢療法醫師診斷的比喻——以及揉合她夢見自己墜入一個深淵而身體融化、前進、迷失的回憶繪畫出來。再細看這些作品還有〈冰火〉(2021)、〈枯榮I〉(2022)和〈冷髮〉(2023)等的原子筆筆痕,原來散發著一絲絲暴力,因為尖銳的走珠無論如何都會多少刮在擦膠柔軟的光滑面上;而有趣的是原子筆的顏色會滲透進擦膠中而隨著時間變色,黑色墨水在擦膠中竟變偏藍,儼如青花瓷面,致使作品過了幾年它的緩慢滲化又會是另一模樣,尤其〈枯榮I〉(2022)那種瘀紫色彷彿已像血管傾注入肉了,令這幅「繪畫」介乎於平面與立體之間,並非像油畫布只為承托顏料,而是它已跟顏料消融一體。
〈點現〉(2019-2023)
石墨和橡皮擦
72 x 73 x 1.5 cm
〈枯榮II〉(2022)
原子筆和橡皮擦
17 x 17.5 x 1.5 cm
〈擦拭新聞:豬籠草〉(2023)
報紙墨水, 原子筆墨水和橡皮擦
57.4 x 38.3 x 1.5 cm
融化、消解、排遣,似乎是張馨儀的創作以至人生的關鍵詞,這些創作簡直是她赤裸地與觀眾分享她的個人歷史,讓人窺探她心靈經歷過的種種創傷和療癒過程,而某程度上透過這個城市的共同回憶與我們產生連結——說藝術能否分擔一個城市的痛楚或許過於偉大,但只希望能夠做到對自己誠實。谷川俊太郎的《定義》,封面寫著「這本書是寫在萬物被命名之前」。給予事物名字就會定下它的意義。現今世界很多人相信是以機械論式地運作,對意義的話語權被解放因而失落,苦難不為了誰,救贖也不等誰;唯有主體性能打破分類和定義,真正地自己建構自己而非實現社會框架下的預言——鳥類不為鳥類學而存在。
〈冰火〉(2021)
原子筆和橡皮擦
47.5 x 43 x 1.5 cm
〈枯榮 I〉(2022)
原子筆和橡皮擦
17 x 17.5 x 1.5 cm
〈冷髮〉(2023)
原子筆墨水和橡皮擦
53.5 x 51.5 x 1.5 cm
(本文所有圖片由Ora-Ora 及藝術家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