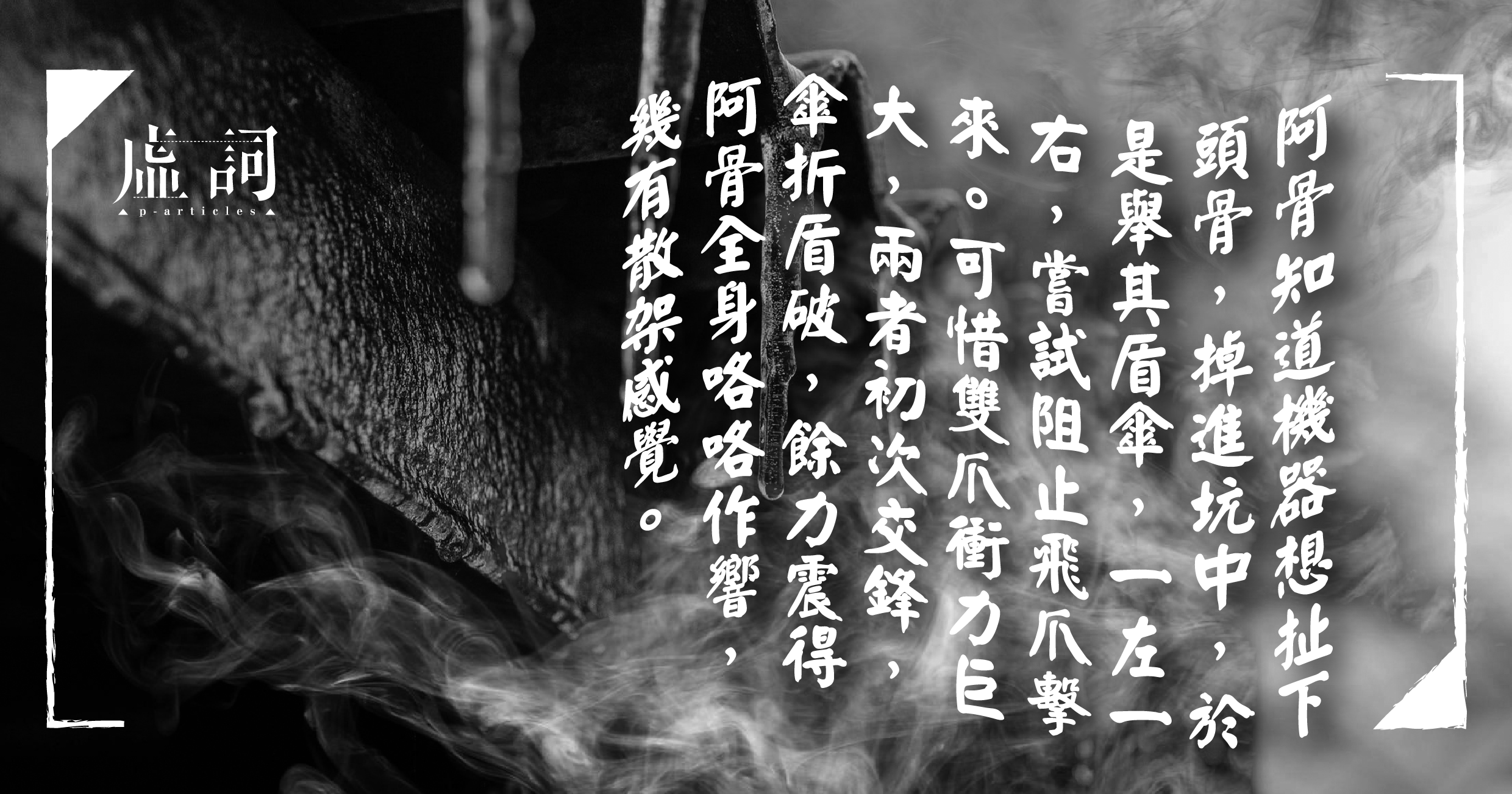暗途夜雪
「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喲!好了好了,終於醒了。」某君意識恢復後,發現躺在一葉扁舟,四周霧影重重,稍吸霧氣,立時咳嗽不絕,喉嚨欲裂,與之同時,雙眼甚為刺痛,似有眼水直流的感覺。「看吧!果然還未適應。不過還好,總能適應的。我們都是這樣產生抗體的。」某君待刺激症狀稍微舒緩,定下心神,眼前坐著兩名九十後中年大叔,但某君原本並不知道今夕是何年,只在兩個中年大叔的談話之中,提到甚麼九十後徐徐老去之事。某君轉過頭來,看看雙手,又環顧全身,居然血肉全無,只剩一副骸骨。「不好意思,那件事之後,你和其他人一樣,都成粉了。還好你死剩一個頭顱,意識大致完整,只是記憶倒散了絕大部分。我們當時慌忙掘開附近墓地,把各種手手腳腳,胸骨肋骨拼成一副新架,再安上你的頭骨,讓你暫時有個歸宿。」兩人一人一句,聽得還以為出自一人之口。「所以我只是一部拼裝車?」某君凝視水中是自己但又不是自己的倒影,揮著長短不一的雙手說。大叔甲以為某君心有不滿,安慰道︰「別這樣嘛,起碼還有個頭是你的,如果不小心連頭也炸了,意識消散,找不回來,你就真的死了。」他說完,大叔乙自口袋中取出一個發光小圓,說︰「來!這是你小部分記憶,那件事後,每個人的記憶都隨著形軀飄落個處,你別看這連杯水車薪都不算,我們可是很艱難才保存下來的。」某君這下才意識到,這兩人所說的那件事,甚至自己絕大部分記憶,都拉不起半點有用的片段。看樣子,中年九十後只組裝了他的形軀(或者說,組裝了他的,但又不是他的形軀)﹑保留了意識,但沒有找回記憶。接過大叔中小圓,光球隨即自左手手骨頭,順著腕道,直通腦袋,片斷陡然在腦中變幻開來。可惜這段記憶極短,不過十多分鐘左右。記憶中,某君只記得自己呆呆地看著眼前白光,自強烈閃現後,嘎然而止,腦袋劇烈炸裂,幾乎失去意識,好容易才喘過氣來,某君居然還有呼吸?或者還以為又呼吸?「別急,過多時你就習慣了。」大叔甲說。
舟子泊近岸邊密林,大叔著其舍筏登岸,往林中而去。他瞥了下夜中林子,已覺衰敗死寂,而無數密枝鬼手,直指天際。夜空層雲暗紅,星月循影,厚雲之間,總聽見隆隆作響,沉悶翻湧。他一腳踏岸,林中開口處吹來一陣腥風,風中猶疑夾帶幾段女聲怨曲,環回淒尖,攝人心魂。他下意識就慫了回去,不肯下舟。兩位九十後往他肩上緩緩一推,力道不大,他卻不由自主地飄了出去,落在岸邊。「不好意思,我們瞭解你的心情,但是你自己的記憶,要你自已找回來,我們幫不了你。」九十後說。「那我放棄我的記憶,可否讓我回來?」某君說。「這個不行!那樣我們很難做,況且,哪有人不想找回身世?」九十後說。「但,但是,你們看看,」某君猛然揮著自己的白骨雙臂,反駁道﹕「我還是人嗎?既然你的前提不存在,所以我是不是可以回去了?」九十後說:「其實你真的是不幸中之大幸了,事件之後,基本上你還能擁有自己的意識,萬中無一,好好珍惜。你的記憶要靠你自己,不能指望我們幫你,也不要指望我們幫得到你。況且,你在林中,還不一定找得到記憶。不過起碼,你能嘗試找到答案。」九十後說完,掉轉舟子,駛回水中,吟著歌謠,消於霧色。某君傾力細聽,只知什麼「誰看青簡一編書」什麼「雨冷香魂弔書客」,但聽不清所誦完整內容。
某君不想進去,但又不能離去,只好頹坐岸邊,胡思亂想。首先是稱呼問題。某君當然不記得自己身份,可是要如何用一個能指,指涉自己這所指,還是需要一個名字稱號。那該自稱什麼?既然自己只有一副骸骨,就簡簡單單叫「阿骨」吧。但阿骨究竟是男是女?是老是幼?是高矮還是肥瘦?形軀是組裝的,如何分辨前世今生?當阿骨還在左右互搏,水中突然翻滾湧動,卷起一陣陣浪花。阿骨下意識一驚,連忙後退幾步,但眼見遠方浪勢越來越大,料想不對路,轉身就逃,幾個箭步,遁入林中。
阿骨拖著拼湊出來的骨架,步履不平,一高一低,緩緩行走暗林。路上沒有半點光微,亦無法依賴天外星月,蓋林子枝葉蓬盛,千重萬疊,天色盡隱,無以穿幽。甚至星月本身亦未堪足持,其為雲湧所沒,暗淡遁影,一無所見。阿骨只好在暗途之中摸黑前行,觸碰到甚麼就倚靠甚麼,以支點跳支點方式,步步為營。譬如扶著一樹,再伸手探向四周,摸到實物,就移至下點。實在一無可倚,就俯伏地上,摸地板而行,直至有物為止。方向?座標?時間?今昔兮何夕!甚至阿骨有時會懷疑自己根本就沒有移動,因為視覺早已缺席,上下左右,前前後後,俱為黑棉一團。雖在移動,但視覺沒有證據判定移動。可是,無法判定移動,卻始終還再移動!好像好繞口,正唯思緒混亂,形之於言,纏作一團。想這麼多做甚?阿骨忽然覺得自己愚笨可笑,因為手腳真的有在摸爬嘛!也不知道走了多久,時間在推移,亦在凝滯,方向在轉變,亦已固定。舍卻殘軀,無物可戀。
行進半途,忽焉有光,轉角之處,浮動幾絲微弱淡綠。本來混沌無物的旅途,此刻終見光微,陡然一喜。轉過彎後,一排昏燈勾勒出夜路輪廓,方向地理也漸次可見,一切恍惚有歸來感覺。但好快,阿骨又陷入漫無邊際的沉思。前路鋪排極度整齊對稱的石階,其打磨光滑,幾如石鏡,收納這個詭異世界的同時,也反照世界的詭異。路的兩旁豎著排列整齊的「燈柱」。不過所謂「燈柱」,只是立著一條鐵枝,枝上撐著一個人類頭骨。骨內皮肉早已消亡,只有綠焰磷光,尚且燒湧。光自空洞眼眶散落四處。回想起那兩位九十後的對話,提及「那件事」後,阿骨原有肉身四散成粉,幸好還剩頭骨,保留原有意識。除了頭骨外,阿骨極不協調,極不統一的身軀,其實來自多人拼裝。而眼前這一排頭骨燈焰,究竟是否當初跟阿骨一起參與事件的同伴?是不幸沒有被救,故而成為暗途之中詭異又可怖的暗光?「是否意識也不存在了?」阿骨走近其中一座焰燈說。焰燈頭骨空空,焰火徒轉,並沒有回答阿骨的疑問。
一陣腥風吹過,送來幾陣淒怨笛聲,暗路遠處,大隊儀仗自陰影出來。說也奇怪,儀仗陣容盛大,服飾都是花團錦簇,以為喜慶而來。但怎麼會在這個光景,這個場景,有人慶祝?是有什麼可喜可賀?阿骨盯著儀仗中間的巨大祭壇,壇中供奉各種香果祭品,但上座卻空設一位,大概本來應該有座神像或者其他圖騰。或許祭壇太過沉重,抬壇之士,移動緩慢,前後之輩,亦唯有放慢腳步,尋求步伐一致。結果自遠方看來,是一座龐然巨獸,蹣跚而至。不過這麼重要的神壇,為何神像始終缺席?最重要的主角,反而消失了?思量之間,儀仗之中緩緩走出一名婦人,拉阿骨到旁邊。阿骨打量婦人,婦人也打量阿骨。這人一身古裝,但分辨不出典自何代,即使濃妝豔抹。依舊掩蓋不了妝容之下的瘦弱慘白。而頸上絲巾,似乎故意有事隱瞞。但阿骨依然搞不清楚為何婦人依然注視自己,因為自己只是一副骸骨,任何衣衫皮囊,形相幾乎盡去。「我是不是本該認得你?」阿骨說。「唉!」婦人輕歎一聲,悠悠說道:「太平之世,人鬼相分,今日之世,人鬼相雜。君不存形軀,皮相盡亡,鬼不可觸而君可觸;人有面目而君無面目。敢問郎君,今宵應歸何處?」「其實,其實,我是想說,我還是不要那麼文縐縐的啦,我……我很簡單……就是……就是說,我是來找記憶的,剛才有兩名九十後阿叔推我來這裡,本來我不想來的。」阿骨下意識的相組織文縐縐的句子,但不知道為甚麼,一句也說不出來,只好口吃地回答婦人。婦人指了指神壇吉位,「記憶?他本來會在這裡的,上元之時。」「他?他是誰?」阿骨期待答案,但總是事與願違,婦人答非所問,模糊了阿骨重點。「等等,不對,我該是真的認得你吧?你跟我對話,也因我們相識,或者曾經相識?」阿骨看到婦人身上紫衣、腰間銀魚、手中淨巾,突然若有所思。婦人淒然說道:「故園已逝,故人何去?日月流邁,行路當難。」說完,輕揚雙袖,飄然遠去,不加告別。阿骨呆著半響,直至儀仗遠去,又歸入沉寂。
是重尋舊路,還是望新途而去?阿骨本來很不情願地踏進林子,但經過剛才奇景,有再想深一層,是否還有其他光怪陸離的東西?如果我的記憶就在林中,那麼我的經歷,應該也是身處怪現狀之中?反正現在自己只剩一副骸骨,而這又有一條頭骨燈路,不如……
沿路走去,無端飄來點點雪花。阿骨伸出手掌,任由雪花飄在手上,只覺雪花並沒有溫度。同樣地,阿骨也因此留意到,那些頭骨焰燈,居然也沒有半點溫度。難道是我沒有通感?不對,明明風就是腥的,怎麼可能?但仔細端詳一下,手中根本就不是雪花,而是灰燼。抬頭望遠,半空都是密密麻麻燼絮,只是視覺提示就是雪花,但其實並不是雪花。是不是應該這樣理解?阿骨又再問自己。怎麼進林子以來,不是發問,就是沉思?不然就是不解。不是要尋找記憶嗎?怎麼越來越困惑和迷茫?焰燈之路終到盡頭,或許答案就在前方?然而並不是。阿骨發現這條路導向一片巨大空地。地上一片狼藉,歪歪斜斜地散落各式各樣的裝備,面具、盾牌、槍支、石塊、長棍、短棍,不一而足。就算頭盔,都分成好幾種。阿骨拾起一頂面具,仔細端詳,近臉頰處好像有破口。本向靠近查看,沒料到破口處突然湧出一陣白色煙霧,阿骨被煙霧所熏,雙眼劇烈刺痛,胸口鬱悶,幾欲嘔吐。而過不多時,又開始感到眼水鼻水嘩嘩流落來,跟當初在小舟醒來之時相似,看來阿骨尚未適應,但能夠適應,又是經歷過怎樣的痛苦?但其實一切是阿骨的錯解。阿骨就變成阿骨了,殘軀空空如也,還有什麼東西可以嘔?有什麼液體可以流?別說鼻水眼水,血水也沒有半滴。阿骨不禁失笑,自己似乎還殘留生人感覺,總是學不懂接受現實?但現實已成一副白骨,而這副沒有肉的軀體,居然還有意識,還能行走?荒謬已成現實,現實只是現實。阿骨收拾心神,瞥見空地處似乎有個箱子,走進打開,居然是一整箱剛才那種面具,所不同者,似乎箱子裡的貨物。是完好而尚未開封。所以阿骨在箱子裡找到了面具的說明書。原來這款面具的臉頰位置有暗門可以吸收四周氣體,等近身搏鬥的時候,再把儲存在面具裡的氣體釋放出來,打對手一個措手不及。但剛才破損面具的經歷,阿骨總覺得現實和聲稱蠻有落差的。
燼雪越下越大,漸漸在阿骨身上纏積粉塵,呼吸亦覺窒礙,不甚順暢。沒有辦法,阿骨撿起地上裝備,帶起頭盔面罩,撐開長傘,暫時阻隔灰燼困擾。阿骨有先前經驗,不想再拿那種會吸收氣體的面罩,而是換上了其他牌子。但面罩一換,就發覺面罩和頭盔不是一式裝備。因為阿骨嘗試拉下頭盔上的擋板,但拉到一半,就被面罩突出的部分卡住。應該是有在燒東西吧!不然漫天飛燼,從何而來?阿骨細視燼雪飄來的方向,多源自一處,可能前方,就有答案!阿骨再拾起一塊圓盾,舉盾撐傘,走向疑似源頭。
地上出現一大片陷坑,坑內燃著熊熊綠焰,雖然跟之前路上的骨燈相似,但陷坑裡火勢高漲,骨燈反而顯得很小兒科。坑內堆積成千上萬的頭骨,在焰海中霹啪爆裂,不絕於耳。頭骨不耐高溫,不時發出碎裂成粉的清脆聲響。頭骨成粉灰之後,大片大片飄向半空,或與雲湧共色,或散落林中。其實,那萬里沉厚彤雲,會不會就是頭骨灰塵凝聚而成?所以遮蔽星光,居然以千萬人頭為代價?阿骨再次回憶起那兩個九十後大叔的話。「那件事」是甚麼事?身體為甚麼會四散成粉,而需要以不同人骨拼湊?為什麼頭骨沒有碎裂,失去記憶而保存意識?會不會,遮蔽星光的厚雲,其實就是骨灰凝聚而成?阿骨再次記起那兩個九十後的話。「那件事」是甚麼事?身體為什麼會四散成粉,而需要以不同人骨拼湊?為什麼頭骨沒有碎裂,失去記憶而保存意識是大幸?阿骨有個很恐怖的猜想,難道曾經,我也幾乎不幸成為坑中一員,意識隨骨消散?但白骨先前也是人吧?阿骨倒抽一口涼氣,又感到一陣寒心解日出現流冷汗的感覺,身體激動得無法自已。雙手瑟瑟發抖,撐起之傘,如風中殘花,搖搖欲墜。「一夜東風落,千里百花凋」。
阿骨留意到,陷坑兩旁,一左一右,各放置一台機器。它們源源不斷地將無限頭骨傾倒進坑內。阿骨不知道機器什麼時候開始運作,只是感到好像已經天荒地老。兩部機器,其狀如獸,一台如虎而犬毛。人類面目,虎貓四足,牙齒又如豬畜。有尾甚長,不知確數。另一台則龍首猿身,渾身毛竅。兩台機器隆隆作響,不斷自口中往坑內吐出白骨。或許早自洪荒上古,機器和巨坑,就已經存在。而送骨燒骨的工作,大有永夜萬古之勢。阿骨走近機器,上面已經堆滿了骨灰粉塵,大概厚至數寸。阿骨用手輕輕抹開,機器上面歪歪斜斜地寫著不知所云的文字。其中一台寫道:「楚以名史,主於懲惡」;「能逆知未來,故人有掩捕者,必先知之。史以示往知來者也,故取名焉。」所以機器到底叫甚麼名字?阿骨走到第二台機器,再次摸走粉塵,上面則提到「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奇怪,明明機器就不是這樣的形狀。思疑之間,兩台機器忽然併發紅光,如舞臺射燈,照向阿骨之頭。儘管阿骨戴了面罩,強光仍談令阿骨幾乎撐不開眼睛。大概機器鎖定了目標,尾巴像是收到指令,尾端化作巨爪,抓向阿骨頭部。阿骨知道機器想扯下頭骨,掉進坑中,於是舉其盾傘,一左一右,嘗試阻止飛爪擊來。可惜雙爪衝力巨大,兩者初次交鋒,傘折盾破,餘力震得阿骨全身咯咯作響,幾有散架感覺。而阿骨身體不由自主地向後飛跌,直接撞上林邊大樹,方才止住去勢。阿骨剛重拾心神,雙爪又已急至,閃避不及,頭盔面罩俱被扯下。阿骨眼見不能硬接機器攻勢,待機器二度進逼的空隙,轉身遁入林中。機爪甚大,轉換騰挪,時有卡撞不順之處。反而阿骨只是一副骨頭,身法連換,多能閃躲。不過機器始終是機器。論耐力速度,阿骨依舊無法戰勝,是以相互抵消之下,機器骸骨,倒鬥了個叮噹碼頭。
僵持之間,林子密度漸見疏落,阿骨忽見前方又是一片廣闊空間。心想如果林子已盡,空曠之處,無險可守,何以擺脫機器糾纏?機爪在後面緊逼,隨時有得逞危機,是以無法放慢腳步。前方雖知是死路,但卻又不得不急步向前。無計可施之際,幸而察覺越近空地,機爪速度開始有規律地下降,待林路盡處,咋現一圈圍欄,鐵門高大卻殘破,沒有上鎖,阿骨僅用慣性衝力,就已撞門而入,倒在一旁。機爪在那瞬間急速收掣,退回林中。一切又歸平靜,起點處的平靜。
大約是座墓園。大門框上,立著一隻寬袍大袖的草人,手中持著鐮刀,不過早已生銹,無法亮起半點昔日的餘光,墓園不遠之處,猶有一群寒鴉,佇立枝條之上,目視草人,蠢蠢欲動而又未能行動,靜態之下,反而像一座座木刻雕像。所以到底是什麼原因,使機器也要讓步三分?然後,這裡是除了林子嗎?阿骨幾乎覺得墓園和林子就是平行時空。這裡天淨雲散,星月返現,千萬珠石,重置玉盤。加之風涼清暢,四境靜寧,久倦疲軀,不知不覺就放鬆下來,頹然坐在一塊墓碑旁邊。可能墓園荒廢已久,碑旁早已亂草叢生,幾乎沒及腰間。荒土之上,數點流螢,其聲怨訴,低語如誦,無端就想起「秋墳鬼唱鮑家詩」七字。阿骨好奇,乘著星光,碑上似乎有字,撥開雜草,寫著長短不一的碑文:
夜色低語微風的墓園
自夢中死去又自夢中醒來
寒鴉死盯寬袍大袖的草人
生鏽的鐮刀亮不起
半點昔日的餘光
露冷濕蘸橫亂的荒牆
來路早已沒去來蹤
星流與月影沉灑而過
竟是這是
第幾個地久天長
無聊端起半碎觸髏
飛灑的塵泥如似
記憶般泛黃
然而今宵是否趕及
枕回昔日的白雲帝鄉
枯葉穿串骨蓋洞空
抬望眼是
停滯凍雲和暫霜
無名碑上刻留無數
殘破而解不了碼的歲月
無根之城懸飛天半
繁碎星燈點燃長夜永央
膨脹七彩望替星羅
獨有欲墜不墜的陰影
徘徊在骸骨的碎念與滯僵
亂蛇歪斜地靜躺今宵風涼
砌合的拼圖再度
消散成遍地長爪之句
還有那半片
夢破的殘塘
病紫觸手的海灣上
童話到神話的距離
半面觸髏的人魚蜂圍著
章魚神像的礁石歌唱
一片尖懼的夢囈低語
鬼海襲噬而來大片黑蝗
城暗鴉飛草人失守
滿眼山河只剩下
一寸墳堆以及
一副骸骨
一切的不朽都已朽去
已死之骨何可再死
蝗霧扯盡風勢
等一個必然瞬間
骨墓與碎念一同消亡
肋骨緩緩拆下心旁
憑空划過半圓磷光
微弱的星火自濃黑之中圈闢
出黯淡啞黃的小角一方
那腐朽將折的骨燭
以及無盡的蒼茫
碑文下方,題為《夢骨賦》。墓園和草人,應該就是身處之地了。寒鴉就是墓園之外那群疑似木雕。「無根之城」?阿骨視線移向離火之位,萬裡長天,赫然懸浮一座搖搖欲墜的七彩之城市。「章魚海灣」、「半面人魚」?阿骨順著風聲送來的潮息和歌鳴,果然看倒一座章魚神像塞在海灣入口。神像高大異常,連灣邊海崖,亦未及其高。而單單立在海中,已占去半個海灣海口。阿骨視力突然無限進化,神像之下,是無數圍著神像的魚人,其歌不絕,但尖銳刺耳,驚心動魄。人魚一面是容貌姣好、清麗秀氣,另一面則是皮肉銷盡的白骨。而骨化似乎有蔓延的跡象。可能是受神像腐化影響,但人魚對神像的沉醉迷戀,似乎無法自拔。
骨頭應該是指自己吧?畢竟賦中的墓園白骨,除了自己,別無他物。「長爪之句」?是剛才腦海中的「秋墳鬼唱鮑家詩」嗎?若一切如墓誌所言,那麼下一步就是?阿骨很塊就想到答案,而答案也很快成為答案。海灣吹來大片黑蝗,草人瞬間被海潮淹沒,鐵門傾折,噬向阿骨。阿骨伏在地上,雙手抱頭,任由黑蝗鑽啄啃蝕,心中之存一個念頭:不要被搶走頭骨。但這副殘軀坦度幾乎為零,數秒下去,已感倒幾處碎裂。墓碑最後一段說了什麼?阿骨摸向胸旁,忍著痛楚,啪的一聲,折斷一條肋骨,憑空一劃,骨頭應聲燃起,密密麻麻的黑蝗,立時後退,劃成了一個小圓。肋骨火炬光芒暗淡,火苗隨風搖曳,行將就熄。阿骨微微一笑,代骨燭將盡,又拆一根。這樣越拆越少,骨架也越發鬆散。到得後來,整個下半身都燃燒殆盡。上半身則剩肩旁以上,還有粘在肩膀的雙手。阿骨笑得發瘋,仰天長嘯,雙手燒剩單手,整個身軀都塊燒盡之時,光焰越來越微淡,圈子越發縮窄。黑蝗則步步進逼,準備再次襲來。阿骨趁著手臂骨燭將滅之際,沒有燃其另外一隻手,而是舉起單手,往頭骨一劃,頭上瞬間點燃。阿骨的意識越來越模糊,淡黃的火光,永夜只是泛起半點漣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