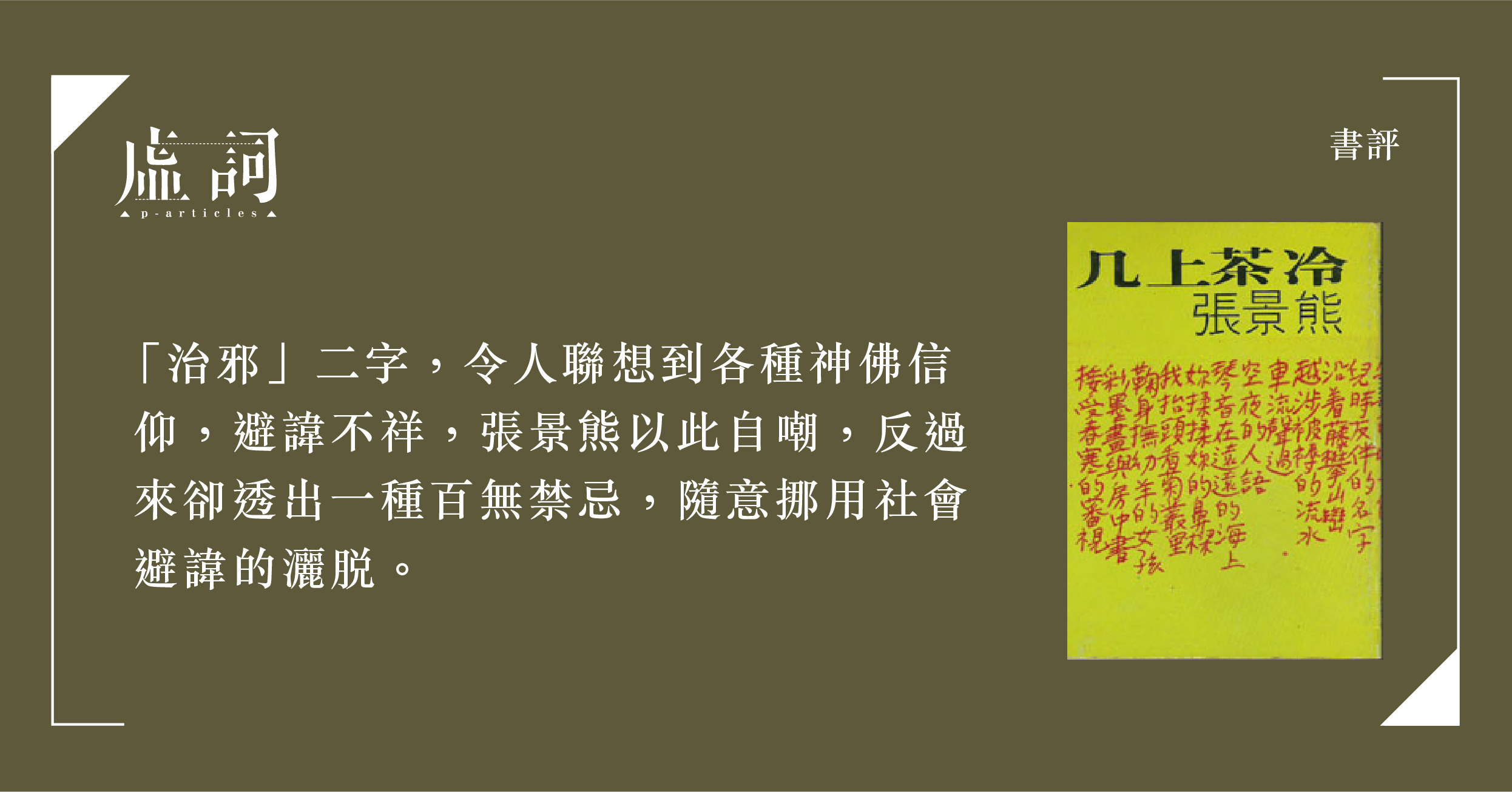日本之美︰川端康成的美麗與哀愁
從川端的成名作,1927年出版的《伊豆的舞孃》到1972年逝世為止,他為世人留下了「如何閱讀日本之美」的一道窗口,瑞典學院頒發諾貝爾文學獎時的評語也圍繞著文學中的日本性,從血緣關係至古典日本美學等等,並認為川端「以敏銳觸覺、高超敍事技巧,表現了日本人的精神特質」。這一切都可以從《伊豆的舞孃》開始追溯,這部作品後來無數次被翻拍成電影、電視劇、廣播劇等等,第一次翻拍早在1933年已由五所平之助導演,是極其珍貴的歷史材料。而電影節發燒友(HK Cine Fan)舉辦的「虛無之愛.幽玄之美——川端康成文學映畫」活動,將於今年四、五月放映這部珍貴的電影。 (閱讀更多)
空間化的歷史詩學——再談《盧麒之死》
書評 | by 楊焯灃 | 2019-04-03
這次想談的是黃碧雲《盧麒之死》的、我姑且稱之為「空間化的歷史詩學」。如何不以時間而以空間為主軸去思考歷史書寫? (閱讀更多)
如何浪漫地離「家」出走?——段義孚《浪漫主義地理學︰探索崇高卓越的景觀》
德國思想家暨尼采及海德格傳記作者薩弗蘭斯基,在其著作《榮耀與醜聞︰思考德國浪漫主義》中,發現浪漫可以是對一個新開端的激情,如盧梭去萬塞納途中,在路邊樹下經歷靈感迸發的時刻;也可以是重建精神的盼望,如浪漫主義思想家赫爾德;它可以對於瞬間、恐懼和決斷的崇拜,如海德格、齊克果,甚至曾批判浪漫派的卡爾.施米特,都強調決斷的重要;它也強調超越,如十九世紀德國畫家弗利德里希一幅最著名的畫作,就是一人登上山頂觀看雲海的景色。 (閱讀更多)
傷害:細節的織布——讀梁莉姿《明媚如是》
這部作品所探討的議題其實香港人早已經麻木習慣:學童自殺、家庭暴力、基層困苦、意識形態分歧……甚至可以說是,看到生厭,誰會願意空暇時候還去分擔他人的痛苦?我們連自己的問題都解決不了。但作為一部文學作品,《明媚如是》如何拆解、重組、上色、佈置這些「他人之痛苦」與「個人之體驗」,敲出外殼,擰緊每顆螺絲,讓香港的悲哀面目以小說呈現? (閱讀更多)